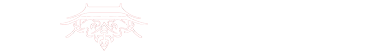餐桌大戏——老北京涮羊肉
中国有句老话,叫“不时不食”,意思就是吃东西要应时令、按季节,一招一式不能乱。这出自《论语·乡党》的一句话,是孔老夫子在数千年前留给我们的养生秘诀,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。说到随节气的变化而改变吃食,老北京人最有发言权,其中例子不胜枚举。比如,立春当日要吃春饼、春卷,即所谓的“咬春”,炎炎夏日则要来上一碗清香解暑的荷叶粥,而中秋不仅要吃月饼,更要品尝应季的石榴、莲藕。至于数九寒冬,还有什么能比涮羊肉更暖胃又暖心呢?
老北京人的饮食习惯,过去多“以羊为主,豕(猪)助之,鱼又次焉”。在老北京的传统里,涮羊肉要在冬至以后吃才是做到了“不时不食”。羊肉性热性燥,春夏吃不仅容易上火,而且还会觉得油腻。因此只有到了冬季,天儿冷,人体寒,正好吃羊肉补阳气,起到温补的食疗效果。且羊肉有利五脏,而五脏热了,人们才能抵御这难捱的漫漫寒冬。试想,在大雪纷飞的冬日,面前的紫铜火锅中开水沸腾,拾起筷子,夹起一片薄薄的羊肉,在沸水里一涮,两涮,三涮,辅之以蘸料,入口即化,慢慢体会其中的清、香、鲜、美,岂不是冬日里的一大快事!
涮羊肉是北京许多饭庄的特色。各大饭庄里,羊肉做法无数,在老师傅的手里总能翻出新花样,或炒,或扒,或烧,但涮羊肉无疑是许多人无法割舍的那一口儿。说起来,北京并不是羊肉的主产地,那这涮羊肉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轨迹,才逐渐征服了北京人的味蕾呢?
涮羊肉,又叫作“羊肉片火锅”,离不开的当然是火锅。这种锅、炉合一,可以随煮随吃的食具,是让羊肉焕发其魅力的不可或缺的存在。要想理清这涮羊肉的历史,不妨先说一说火锅的历史。
时至今日,火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在煎炒烹炸等烹饪技术成熟之前,中国人就已经学会吃火锅了。古代,火锅被称为“古董羹”,因为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的“咕咚’声而得名。据考证,东汉时出现了一种鼎,上面为容器,下面有几个支点。吃东西时,将肉切成块放入上面的容器中,下面架上火,煮熟后就可以捞出放在自己的容器里吃。毫无疑问,这种鼎就是中国早期的火锅。三国时期,有一种名为”五熟釜’的炊具,便是改良过后的火锅。“五熟釜”分为五格,可调五种不同的味道,食客可依自己的喜好分格而食,与我们如今的鸳鸯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经过南北朝、唐宋等数个朝代的历练,火锅不断得到完善,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。那么到底是在什么时候,人们发现了火锅与羊肉碰撞所迸发出来的独特美味呢?
1984年,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了辽代早期壁画,其中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: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,有人正拿着筷子在锅中涮羊肉,火锅前的方桌上摆着羊肉和配料。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关于涮羊肉的最早史料。而比壁画所处时代稍晚一些的南宋,也出现了涮羊肉的记载。时人林洪在所著的《山家清供》中,描述了涮兔肉的制法和所用调料,并题诗“浪涌晴江雪,风翻晚照霞”,以此来赞美兔肉在汤中的色泽如晚霞一般明丽。而在讲完涮兔肉的妙处之后,林洪又添上一句:猪、羊皆可。这便成为了涮羊肉最早的文字记载。但是按照书中记载,林洪是将肉切成薄片,先用酒、酱、辣椒浸泡入味后,再入沸水中烫熟,这与我们现今的涮羊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但不管怎样,涮羊肉这种美味,在辽宋时期就已经印刻在人们的美食记忆中了。
在历史上,鲜嫩可口的涮羊肉不仅在民间广受欢迎,甚至还让许多帝王将相为之牵肠挂肚,历朝历代的深宫之内不乏这小小火锅的身影。要说起皇帝们的涮羊肉情结,首先当数元世祖忽必烈。相传某年冬日,忽必烈统率大军在外征战,一番激战后,部队安营扎寨,打算好好休整一番。厨子们忙着烧火宰羊,欲好好犒劳疲惫的将士们。就在这时,敌军却突然来袭,忽必烈连忙下令部队开拔,可这羊肉却已来不及煮熟了。情急之下,厨子只好将羊肉切成薄片,放在开水中简单烫了一下,撒上调料递给忽必烈。没承想,这羊肉片竟意外地美味,忽必烈吃完后投入战斗,最终大获全胜。后来,元朝定都北京,做了皇帝的忽必烈仍对这薄薄的肉片念念不忘,并赐名“涮羊肉”。从此之后,涮羊肉这种美味就在宫廷流传开来。
明代弘治皇帝曾在御花园设酒宴,宴上便有这涮羊肉。相传,明代文学家杨慎自小聪颖过人,有一天,随父亲赴弘治皇帝的酒宴。宴上有涮羊肉火锅,火里烧着木炭,弘治皇帝由此想出来一副上联,“炭黑火红灰似雪”,要众臣对下联。大臣们无言对之,而此时,杨慎却吟出了下联,“谷黄米白饭如霜”。皇上龙颜大悦,当即赏御酒三杯。
到了清代,涮羊肉可用“盛行”二字来形容,其中皇亲国戚们可谓功不可没,正是他们的推崇,涮羊肉一跃成为官廷莱,这道美味也得以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,并且大范围地推广开来。嘉庆元年(1796年),太上皇乾隆在清宫内设“千叟宴”,主菜之一便是这涮羊肉。
荏苒之间,或因涮羊肉鲜嫩可口之中所隐藏的必然,或因历史机缘巧合之中暗藏的偶然,涮羊肉这种美味渐渐在北京这天子脚下扎下根来。经过不断地自我完善和与当地人口味的磨合,涮羊肉俨然成为老北京人在冬日里最难以割舍的滋味。
来源:王丹 原创